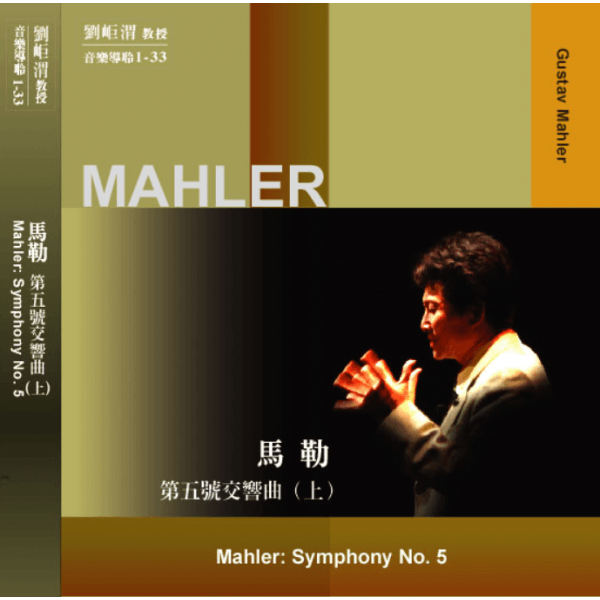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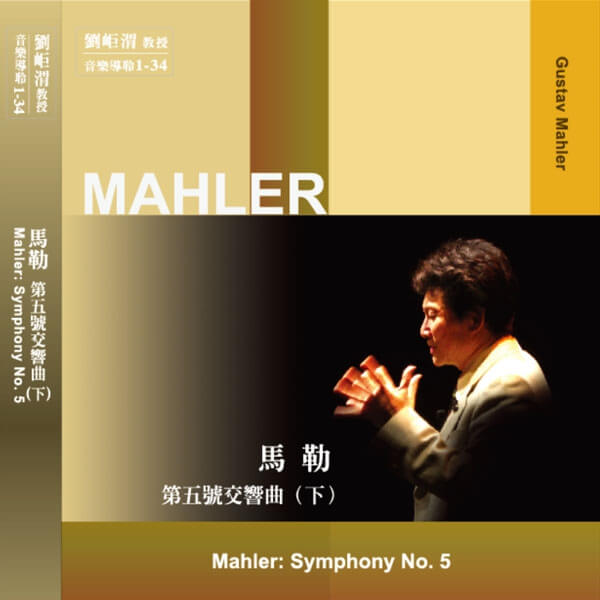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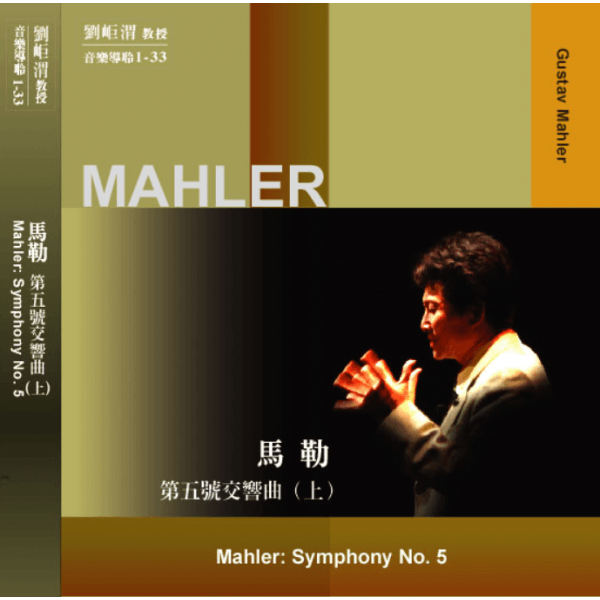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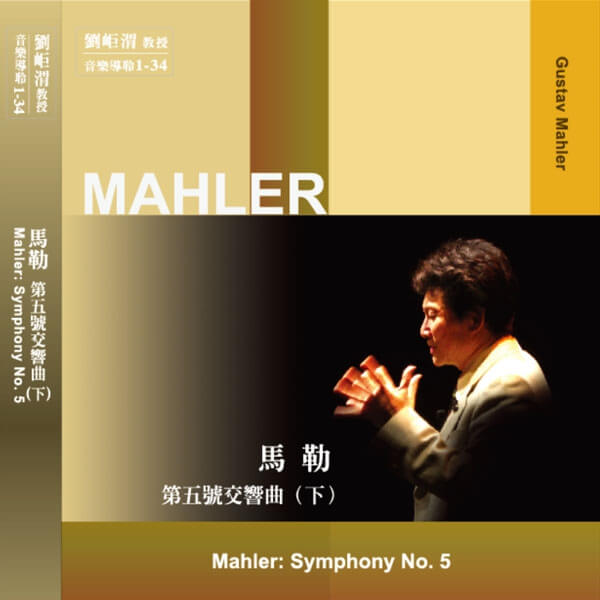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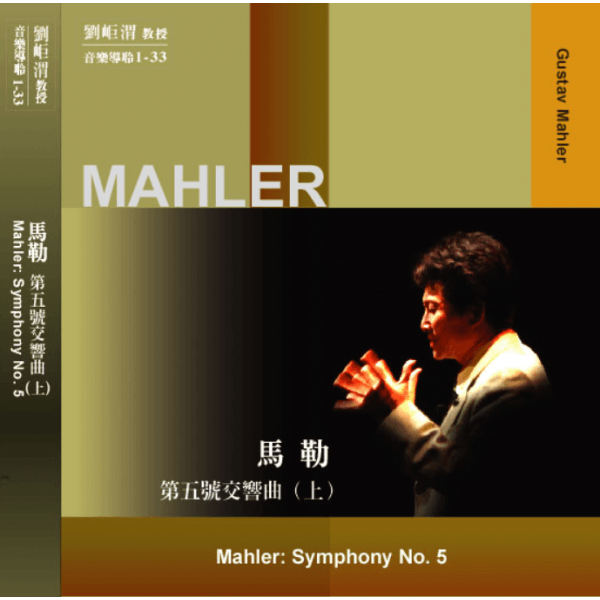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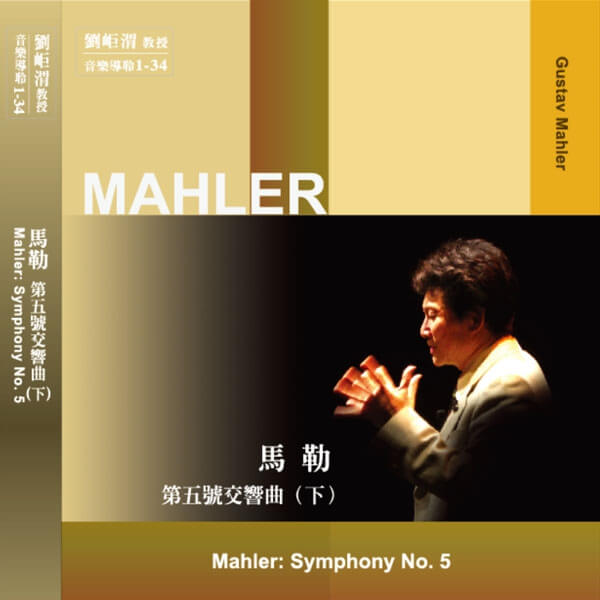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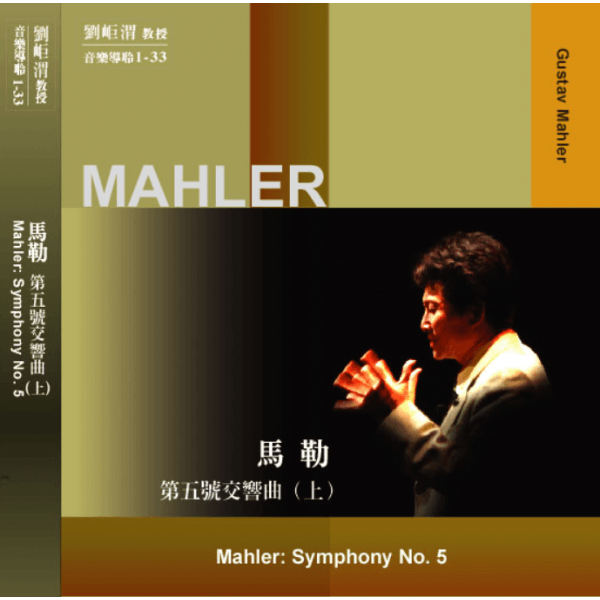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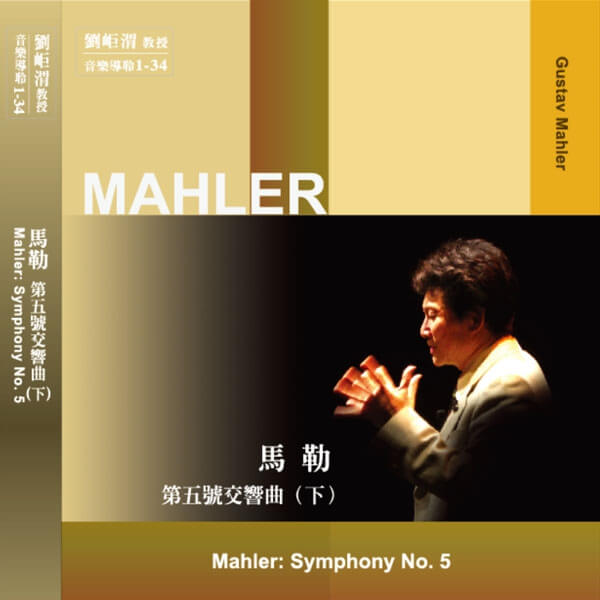
馬勒﹕第五號交響曲(上)
Gustav Mahler﹕Symphony No. 5
DISC 1 1:08’07”
第一樂章 送葬進行曲。精確的步伐。嚴格地。如送葬隊伍般
(Trauermarsch. In gemessenem Schritt. Streng. Wie ein Kondukt)
DISC 2 48’38”
第二樂章 如暴風雨般的激烈。並更加激烈
(Stürmisch bewegt. Mit größter Vehemenz)
馬勒﹕第五號交響曲(下)
Gustav Mahler﹕Symphony No. 5
DISC 1 1:03’36”
第三樂章 詼諧曲。使力地,但不要太急促
(Scherzo. Kräftig, nicht zu schnell)
DISC 2 1:27’45’’
第四樂章 稍慢板。很緩慢的
(Adagietto. Sehr langsam)
第五樂章 迴旋曲-終樂章。快板-遊戲似的快板。精神飽滿地
(Rondo-Finale. Allegro-Allegro giocoso. Frisch)
1901年夏天,馬勒著手進行《第五號交響曲》的創作。忙碌的指揮工作讓他大多只能利用夏天這段期間作曲;到了第二年夏天,他終於完成這首曲子。1904年10月18日,馬勒親自指揮《第五號》在科隆的首演。
儘管分處於浪漫早期和浪漫後期,馬勒的音樂性格方面很多時候很接近舒伯特,亦即,歌曲的精神瀰漫於他的整體藝術表現。交響曲是他作品的主體,而歌曲的抒情性是他交響曲中的基本成分。在《第五號》之前,他的交響曲或者使用自己的連篇歌曲集的旋律(如《第一號》引用《旅人之歌》〔Lieder eines fahrenden Gesellen〕的主題)、或者甚至直接將人聲加入交響樂當中(第二、三、四號),使得他的這類作品具有很強的標題意義,可視為廣義的標題音樂。
與前四首交響曲相比,馬勒在《第五號》這裡卻重新回到純粹的器樂曲,並且大量使用複雜的對位技巧來寫作,如第一、第三樂章的第一個中段(trio)、第四樂章的A段,特別是第五樂章當音樂進入「遊戲式的快板」之際,有一段巴哈風格的賦格發展段落,最後由銅管奏出的聖詠造就繁複又熱烈地結束全曲。馬勒精湛的對位風格管弦樂處理手法在這部作品格外突顯。
承載著厚重的複音音樂的是五個樂章的巨型結構,一般將它們分成三大部分:第一、二樂章;第三樂章;第四、五樂章,大範圍來看,隱含著以第三樂章為中心的對稱性,加上主題材料作跨樂章「交互參照」的現象,後面樂章的主題採用前面樂章的材料,形成一種「循環結構」,讓各樂章之間的相互關係更嚴謹。
在音樂情緒的發展來看,從第一樂章送葬進行曲的悲愴、第二樂章奏鳴曲式的躁動不安與吶喊、第三樂章詼諧曲混合蘭德勒舞曲(Ländler)的充滿節慶氣息、第四樂章三段體近乎病態的抒情性,到第五樂章迴旋曲的熱情激昂,《第五號》完全是典型「世紀末」時代精神的展現。
《第五號》不僅在篇幅上(樂曲長度接近七十五分鐘)符合浪漫後期交響曲的特徵,樂團陣容也相當龐大:包含五、六十位演奏者的弦樂群、十六支木管及十四支銅管、豎琴、定音鼓加六件打擊樂器等,需要近百位演奏者的樂團組成,顯示作曲家對音色及音量變化的要求。馬勒在總譜上一貫地針對詮釋方面做了許多詳細指示,以指揮家的經驗和專業,對自己的音樂所應該具有的音響效果有相當的定見,是故這首曲子自完成後,歷經多次修改,特別在管弦樂法的部分,一直到他去世前的幾個月,才底定了最終版本,足見作曲家對《第五號》在配器色彩方面的重視。儘管樂團陣容龐大,但他並非僅倚賴整個樂團來發出驚人的管弦樂聲響,他也讓樂器的分配使用有更多可能性,以擴大表現幅度。例如第一樂章的第一個中段,音樂的進行採取小號和小提琴的組合進行對位;第三樂章的第二個中段,有寫給法國號首席的獨奏;第四樂章則只留給豎琴和弦樂群來表現透明清晰的優美旋律,甚至到了中段只剩下第一小提琴,可見馬勒對於單純音色的偏好和樂器組合多樣化的運用。
除了管弦樂寫作方面完全是馬勒獨特的色彩之外,所謂典型的馬勒風格在《第五號》這裡值得注意的有:第一樂章,照例是他所喜歡的送葬進行曲,隱含著對生死的沉思的象徵;第二樂章最後頻繁出現的大跳音程,增加音樂的表現力;第三樂章蘭德勒舞曲,富有波希米亞式的、自然純樸的田園風;第四樂章以少數樂器、豐富和聲加上力度變化的漸強突弱,表達濃烈情感;第五樂章最後的聖詠,則讓人有宗教方面的聯想。甫於跨入二十世紀始完成的《第五號》,展現出作曲家對德奧交響樂傳統的懷舊一瞥。(文/殷于涵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