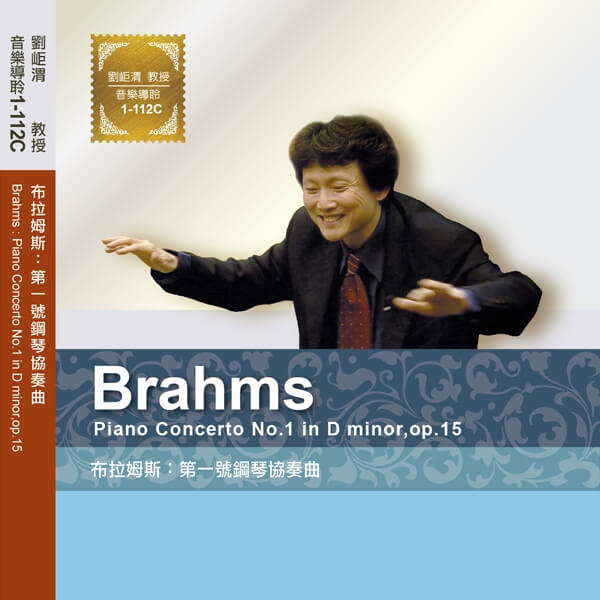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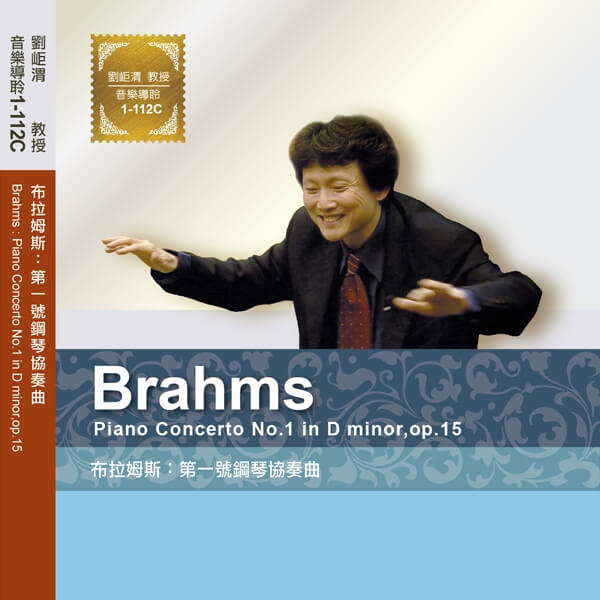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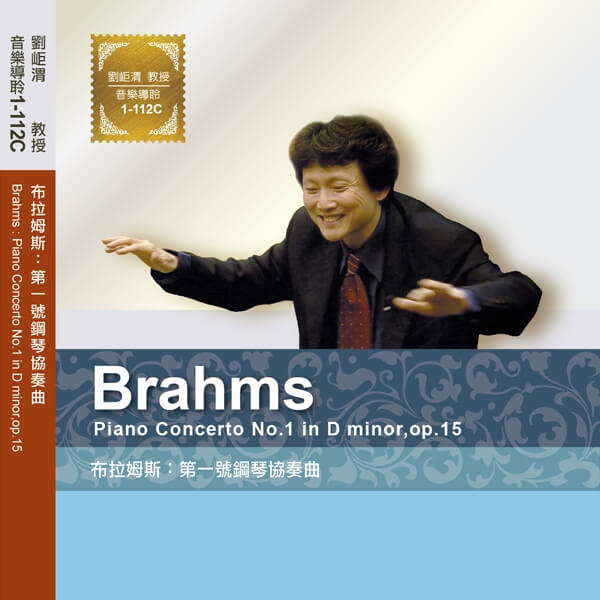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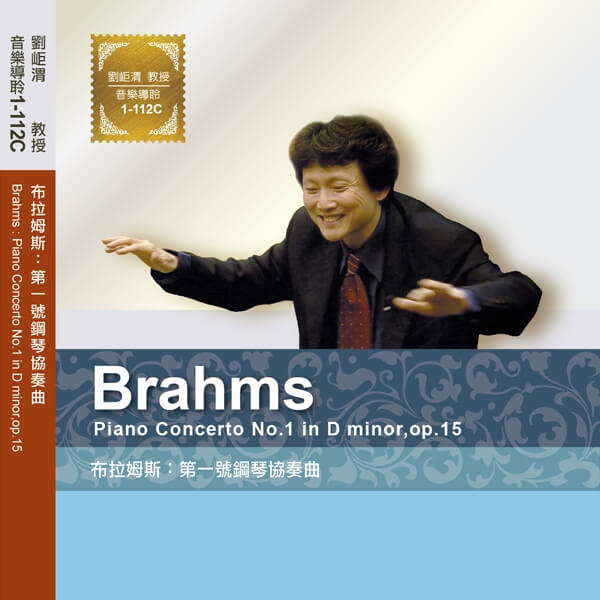
Disc 1 1:12’27”
第一樂章:莊嚴的 Maestoso
Disc 2 55’58”
第二樂章:柔板 Adagio
第三樂章:迴旋曲:不太快的快板 Rondo:Allegro non troppo
布拉姆斯v.s 鋼琴與鋼琴曲
七歲學琴的布拉姆斯,十歲就有公開演奏的能力,年少時還曾因鋼琴音調不準,直接「移調」演奏貝多芬鋼琴奏鳴曲,顯見其絕佳的音樂實力,而他也對寫作鋼琴作品充滿熱情,二十歲以前就完成了三首鋼琴奏鳴曲,其中第三號鋼琴奏鳴曲以五個樂章寫成,相當大膽且獨樹一格。而他寫過相關的鋼琴作品為:三首奏鳴曲、四首變奏曲、五套鋼琴小品集、兩首鋼琴協奏曲及其他室內樂作品等。
布拉姆斯v.s舒曼夫婦
布拉姆斯的成功,絕對與舒曼夫妻(Robert & Clara Schumann)的賞識、力薦有著極大關聯,對恩師抱以無比崇敬之心的布拉姆斯,同時也戀慕著師母克拉拉理想伴侶的形象,1854年,舒曼的精神狀況日益狂亂導致突然投河自殺,雖被及時救起,仍為舒曼一家投下巨大的震撼彈,受到嚴重刺激的布拉姆斯,亦寫下了一首雙鋼琴奏鳴曲,舒曼看到此曲初稿時,稱它為隱藏的交響曲,足見此曲豐富的樂思已超出鋼琴奏鳴曲能表達的範圍,或許就是這樣,此曲才會成為日後寫作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的基石。而投河後便住進精神病院的舒曼,已無法負擔照顧家庭的重責,從這時起,布拉姆斯便擔起照顧舒曼一家的責任,直到舒曼1856年去世。
雙鋼琴奏鳴曲-交響曲-鋼琴協奏曲的創作歷程
1854年7月19日,布拉姆斯寫信給姚阿幸(Joseph Joachim)說:「我想把d小調雙鋼琴奏鳴曲暫且擱下,我和舒曼夫人已把前三個樂章演奏了好幾次,老實說,我並不滿意把這首曲子寫成雙鋼琴曲。」在如此不滿足的驅使下,布拉姆斯開始著手將該曲的第一樂章寫以管弦樂編制,打算寫成交響曲的第一樂章,但年輕的布拉姆斯顯然還沒準備好,他在自己嚴厲的要求下,終究放棄了寫作交響曲的念頭。
1855-56年之間,布拉姆斯曾在寫給克拉拉的信中,提到他對這首未完成交響曲的處置:「我試圖改用鋼琴協奏曲的方式,來彈奏這首命運乖舛的交響曲。當我潤飾修改第一樂章、詼諧曲和終樂章後,才發現它竟變成深得嚇人且非常壯大的音樂,但我的心情卻很舒坦」,1856年4月,布拉姆斯把這手稿寄給姚阿幸徵求他的意見,其後再把第二、三樂章補齊。布拉姆斯第一首規模最大的管弦樂作品,終於完成了。有人曾說,貝多芬二十五歲到維也納時,最初寫下的巨作是降B大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,而布拉姆斯到維也納後也開始動筆,完成本曲時恰巧也是25歲。
不被當代人接受的鋼琴協奏曲
按照布拉姆斯深沉巨大的寫作樂念,應可預期觀眾的反應如何。果不其然,1859年1月22日在漢諾威宮廷劇院,姚阿幸指揮,布拉姆斯親自擔任鋼琴獨奏的第三次預演會上,本曲評價並不高;1月27日在萊比錫由布拉姆斯再次擔任鋼琴獨奏的正式首演,僅有三人鼓掌且馬上被旁人制止,樂評寫著「大眾為之憂慮,音樂家為之迷惘」,「此協奏曲的獨奏部分一點也不優美,管弦樂的合奏則是一連串刺耳的和弦」亦被痛批為:莫名其妙的一團混亂,不和諧音和噪音組成的一片沙漠。
不僅樂評極盡批評,當時許多音樂家如安東.魯賓斯坦(Anton Rubinstein)也認為此曲「在起居室中演奏不夠雅緻;在演奏廳中演奏又顯得不夠激烈;對鄉親而言不夠原始;對文人而言又嫌不夠爾雅。」作曲家拉羅(Édouard Lalo)甚至特別在給小提琴家撒拉沙泰(Pablo de Sarasate)的信中寫道:「我堅持認為當獨奏家站在台上時,就應該由他擔任主角,而不只是管弦樂團中的獨奏者而已。如果獨奏曲的形式不討作曲家歡心,那就寫交響曲或其他管弦樂團編制的樂曲,但千萬不要寫穿插在管弦樂曲中的獨奏片段,我覺得如此安排真是索然無味。」面對諸多惡評,布拉姆斯沮喪說道:「我不過是在實驗自己的感覺。」
繁雜龐大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
為何這首三樂章鋼琴協奏曲會招致諸多惡評?與其繁雜龐大的內容及快速轉換的情緒起伏有關,首先莊嚴的第一樂章,竟是由定音鼓擊出令人震動的第一主題,那鋪天蓋地的沉重感,就如姚阿幸寄給卡貝克(Max Kalbeck)的信中所提到:這個主題是布拉姆斯當年接獲舒曼自殺消息後,在極度震驚的思緒中,腦中所浮現的旋律,然而緊接在逼得人喘不過氣來的槌擊之後,卻是溫暖、剔透的綿長鋼琴主奏。據傳布拉姆斯曾在標示為慢板的第二樂章樂譜上,寫下一段〈迎主曲〉的經文:「奉主之名而來者,當受到讚美。」有人認為本樂章可能是暗示舒曼的不幸,因布拉姆斯曾稱舒曼為「吾主」,用其表達悲痛及追悼之意,不過後來這句話被刪掉了。而另外一說是布拉姆斯寫給克拉拉的信中提及:「我為你準備一幅柔美的畫像,就在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的慢板樂章裡面。」第三樂章採輪旋曲式,由鋼琴複雜的旋律領奏,兩個一明一暗的主題交替著,尾奏前的幻想曲風(Quasi fantasia)則顯示出古典傳統的痕跡。本曲雖名為協奏曲,實則包涵著交響曲的性格,鋼琴幾乎已融入樂團,成為眾多樂器中的一份子,無怪乎拉羅會有上述評價,而我們若能以鋼琴交響曲的角度來欣賞本曲,或許更能貼近作曲者的心思。(文/楊為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