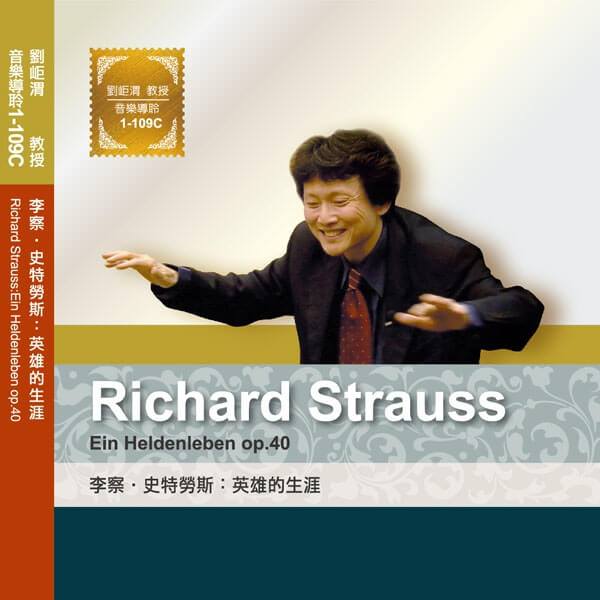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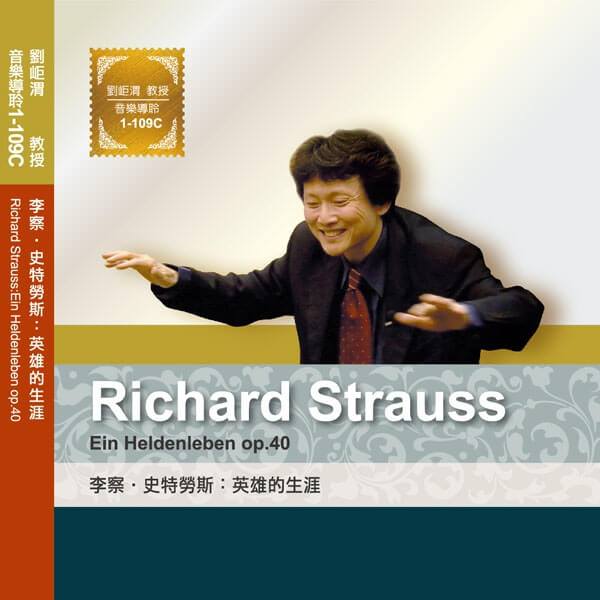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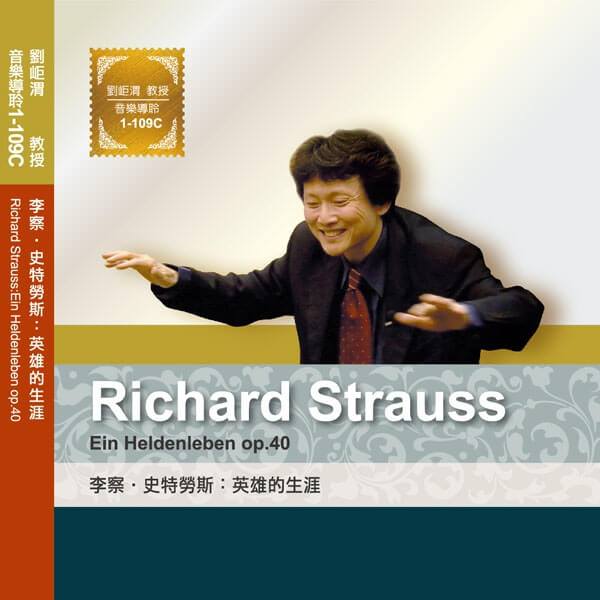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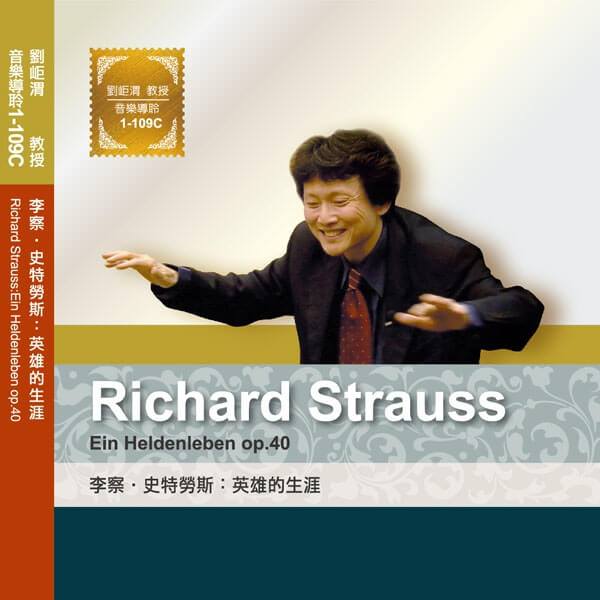
Disc 1 1:18’09”
1.英雄Held
2.英雄的敵對者Des Helden Widersacher
3.英雄的情人Des Helden Gefӓhrtin
Disc 2 1:10’04”
4.英雄的戰場Des Helden Walstatt
5.英雄的和平使命Des Helden Friedenswerke
6.英雄的隱退與完成Des Helden Weltflucht und Vollendung
1898年,時年三十四歲的李察‧史特勞斯創作了《英雄的生涯》,這是作曲家一生中最後一部交響詩,也是成就最高的巔峰之作,更是後浪漫主義及標題音樂的最後巨著。1899年3月3日首演前,其友人於各樂段間臨時加添了六段標題,分別是:〈英雄〉(Der Held)、〈英雄的敵人〉(Des Helden Widersacher)、〈英雄的伴侶〉(Des Helden Gefährtin) 、〈英雄的戰場〉(Des Helden Walstatt)、〈英雄的和平使命〉(Des Helden Friedenswerke)、〈英雄的隱退及完成〉(Des Helden Weltflucht und Vollendung) ,並於當天由作曲家親自指揮法蘭克福博物館管弦樂團演出。
因著這些標題,有人認為此曲乃是李察‧史特勞斯對己身的描繪,狂妄地以英雄自封,透過這部作品向世人宣告自己「英雄」的身分,其實我們大可不必理解太過,創作者自會在作品中投射自己的意念,不妨從李察‧史特勞斯的性格與當時的創作背景來推敲作曲家寫作本曲的初衷。
首先,李察‧史特勞斯絕對是自信的,其自信或許來自絕對服膺且繼承華格納(Richard Wagner)的格局,他曾戲謔地認為,世上只有華格納和自己的歌劇足以登上大雅之堂,也因為他極度崇拜華格納,所以不時可從其手稿和信件中,發現他以與華格納同名而自豪,也常刻意在5月22 日才為作品寫下最後一音,只因那天是華格納的生日。而我們也可以從其1898年7月寫給友人的書信中,看到他對本曲的期許:「我們這個時代,鮮少有機會聽到貝多芬的《英雄交響曲》,因為當代的指揮家們並不喜愛演奏此曲,為了彌補這個遺憾,我譜寫了一首名為《英雄的生涯》的大型交響詩,且同樣將調性安置在降 E 大調上。」
其二,李察‧史特勞斯曾坦言此曲第三段〈英雄的伴侶〉中的小提琴獨奏,表達的是女高音風情萬種卻又捉摸不定的脾氣,而這位女高音的範本,正是李察‧史特勞斯的歌唱家太座!
其三,在第五段〈英雄的和平使命〉中,史特勞斯引用了許多先前的作品,例如:《狄爾的惡作劇》、《唐璜》、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、《死與變容》、《唐吉訶德》、《貢特拉姆》、《馬克白》及歌曲〈黎明之夢〉等主題,而第六段〈英雄的隱退及完成〉則是以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的開頭作結。
以上的種種跡象,似乎都暗喻著英雄就是史特勞斯本人,但作曲家也曾對好友羅曼羅蘭(Romain Rolland)表白:「我並非戰鬥的料,因為我沒有足夠的力量,我並不是英雄!我寧願選擇退場,保持沉默,享受和平。」而這樣的心境無非已在本曲中展露無遺:英雄歷經一番爭鬥,不畏困難立於藝術頂峰,不為各種責難與批評所動,只待功成名就之時,急流勇退。本曲以龐大且嚴謹的奏鳴曲式為基底,搭配出人意料的管弦樂配器,交織出類標題音樂的內涵,或許再佐以其孿生作品《唐吉珂德》,更能完整勾勒出史特勞斯心中的「英雄」形象。(文/楊為茜)